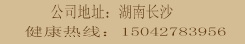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一个阿拉伯男人的爱情故事花花大少苏里门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一个阿拉伯男人的爱情故事花花大少苏里门

![]()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一个阿拉伯男人的爱情故事花花大少苏里门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一个阿拉伯男人的爱情故事花花大少苏里门
这两天总跟人讨论牙齿,使我忆起了一个人,是他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牙齿是人生重要的保养功课。
在我的生命里,苏里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
苏里门应该是索比亚人,可能偏阿拉伯人多一些。
索比亚人是苏丹的典型人口,为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的混血,目前的苏丹应该很难找到纯种的阿拉伯人了,有,但是很少。
第一次认识苏里门是在哪里,已经没有印象了,或者是在我们都常去的那家公司,或者是经理带回来而认识的,他是经理的朋友。
他有着一身古铜色的皮肤,面貌英俊,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健美。
身材健美也是我今天回忆起来才悟到的,当时没觉得,认识了色女总裁女友之后,才知道男人有个翘臀是很性感的,她总是会因此而心荡神驰。
嗯,回想起来苏里门就是有这样的翘臀的,不仅如此,隔着衬衣也能看出那倒三角的健美身形。
他那时候只有二十七八岁,我大约三十三四岁。
从何时起他成了我办公室的常客也不得而知,总之,很快,他就是天天到我办公室“上班”的人了。
刚开始我还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天天来,他告诉我,并且当时在场的苏丹籍女助理们也这么附和,在苏丹,只要是朋友就是要天天见面的,每天说“哈罗”的。
我当时毫不怀疑,但是,今天,当我写这篇文章,回忆起从前的时候,我才开始怀疑,也许这并不是苏丹朋友间的常态。因为哈里德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只是在节假日或者空闲时亲自给我送来礼物,在我这坐上半个小时。
苏里门是一家建筑安装公司的小老板,或许不用坐班使他有如此之便利吧。如许想,心下泰安。
总之他相当于给我当了两年的免费义工,坐在我办公桌对面,随叫随到那种,我遇到的任何困难,他都主动给我摆平了。
他每天上午9点钟左右准时出现,如果上午没出现,下午3、4点钟一定会出现,假如,哪天他没出现,那还真是破天荒了。
我那时候是很忙的,采办贸易、人力资源、厨师、文秘、财务身兼数职,我总是戏称自己为公司的大内总管。这只是一家管理性质的公司,所以并无多少实际性质的业务,但集除技术之外的所有职能于一身,我还是相当繁忙的。不过在苏里门来访的上班时间,我只忙于文案工作,比如说给联合公司批复AFE或者其他各类申请,比如做帐或者整理我的会计档案,比如撰写公司周报月报,比如做月底报表之类的。
我是从小一心二用的人,听着音乐或者广播做作业是常态。
因而当时并没有觉得他的到来影响了我的工作,总之边和他聊天边工作。
他的英语比我好,那时候。
所以他常常教我英语和阿拉伯语。在他的帮助下,我的英语口语能力提高得很快。
记得那时候,《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很流行,我放来听,他说,他的中文CD有这首歌,他姐姐听了都哭了,但是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我认真地翻译了这首歌的歌词,用黑色签字笔书写在白纸上,并配上了符合此情境的画,送给他。
有一次我比较闲,画了一张他的素描送给他,他兴奋极了,说要拿回家给他妈妈看,还要珍藏一辈子。
这是我唯一能想起来的为他做过的两件事了。
而他为我做过的事却是数都数不尽的了。
他是个花心大萝卜。
他常常说,阿拉伯男人的心有四个心室,每个心室能装一个女人,所以阿拉伯男人能娶四个老婆。
他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
我听了一笑置之。
说实话哩,人的心里到底有几个心室,我是搞不清楚的。但是我自己是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爱上四个人的,没准一辈子能有四个丈夫,但是一时间于我,哈哈,是不可能有四个丈夫的。
他说,女人不能同时拥有四个丈夫的,那样会得病。
我吃惊的望着他,问:“真的吗?!”
哈哈,我是真不知道耶!
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呵呵,虽然我不想有四个丈夫,但是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有个答案。
他还跟我说是医生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胡扯。
他有两个女友,他是很坦白的人,两个女友他都有SEX。
这在苏丹可是大逆不道的,如果有人知道这些个女人婚前就有性,一定会被乱石砸死。
自然我这个外族女人是不会胡乱说话的,保密也是我身为资深财务人员的基本素质。
他的女友之一是苏丹首富的女儿,她的女友之二是资深牙医。
当然富人是可以很容易解决处女问题的,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曾请他和首富的女儿到驻地来吃饭。哈,这算是我为他做过的第三件事吧,很庆幸,又想起来了一件。
他和首富女儿是我们那的常客,每次那个美少女都是开着很发飚的不同的跑车或者越野来的,当然我不懂车,值多少钱我是不知道的,只是公司男同事们看着车露出艳羡的神情议论,我想那些车应该是价值不菲的。
他是想和这个美少女结婚的,只想和牙医SEX。
所以没有人知道牙医的存在,除了我。
虽说阿拉伯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但一般他们还是只娶一个,因为不想有更多的麻烦。
他内心深处希望找个外族女人,因为外族女人没有行割礼。
他向往没有行割礼的女人。
这样的社会,哪怕是富商的女儿,也是无法避免残忍的割礼的。
请他和女友吃饭,我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们十点钟到访前,我已经开始忙了,一直到十二点钟吃饭,我没有停。
吃完饭,他问我,你每天都要花费这么长时间做饭吗?
我说,是的,差不多吧,中国菜是比较费时一些。
他感慨为什么中国人要在吃饭上花那么长时间。
那时候,在苏丹,条件很艰苦,我们是没有厨师的,他知道我为大家做饭。
从什么时候起,做饭成为我一个人的事,我也记不清了。
总之经理没有命令过,也没有人要求过,我应该也没有主动请缨。
但是在那的中国男人们不会做饭。
开始我记得是吃餐馆的,什么时候变成我做饭,我真是记不得了。而一旦开始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最终成为我的份内事。
每天早上我5点多就起来给大家煮稀饭,再把前日蒸好的馒头花卷或者包子热上,同事们起来之后就可以吃到现成的了。
中午因为时间很短,我只是变着花样做面条而已,素菜的肉丝的或者西红柿炒鸡蛋的。
晚上我一般会做几个菜,比较耗时。
吃完饭,我会边听着音乐边揉面。发面的时候,去唱十来首卡拉OK,苏丹由于天气热,面一般50分钟就可以发好。然后就可以做好馒头或者包子上屉蒸了,香喷喷的新鲜馒头出炉,总是诱惑着我去咬上一口。
每次我都准备好三天或四天的量,但无论我做多少,从来都是只能用两天。
我知道馒头被公司的苏丹员工偷吃了,尽管我给他们底层人员员工工资在当地已经很高,但是他们还是只能一天吃一顿饭,这是清洁工哈里发告诉我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负担很重。
不过,哈里发,现在在美国了。
自从请苏里门吃过一次饭以后,他就常常请我吃饭。
经常晚上下班时,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走,我请你吃饭,今天,你不用做饭啦!”
我知道,他认为我给大家做饭很累,他想减轻我的负担而已。
我说,“不行啊,我要给他们做饭。”
“那我就请全体一起去吃饭。”
我推迟不过,只有顺从。有时候他就会请大家集体聚餐。
他请我尝遍了苏丹的美食,而且不止一次的重复去尝。
他也被我抓过差。
那是一个节日,记不清是什么节日了,公司男同事们都集体出去吃饭了,留下我们三个女士。
那两个女士都很丧气,很气愤,问我能否找到人请我们吃饭。
我能够想到的我不用有负担的去找的人,好像只有苏里门,我知道,他的一切付出都是不需要回报的。
我给他电话,问他能否请我们这些女士吃饭。
他在二十分钟后到了我们的驻地,带我们去吃印度餐。
还记得饭桌上,他说的关于伊斯兰教对于外教的人们的最终下场的描述。
他说,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死后会受火刑。
哈哈,那分钟我立刻觉得自己成了女巫,已经被执行火刑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家伙实际根本不信教,别看他是穆斯林。
很多个节日,他都带着苏丹的节日传统美食来看我,他说每当想到他们欢聚的节日,是我们寂寞的时分,他就会难过,所以就带着美食来安慰我们一下啦!
哈哈!
也经常会在节假日和周日的时候,接待他的来访,有时他穿着白色的长衫,有时穿着休闲便装。
我们比赛打乒乓球,总是说,十美元一次,谁输了谁付钱。
我从来没有输过,他也从来没付过钱。
我的反抽他从来接不住,我是擅长打反手球的。
学会了发球用英语如何说,呵呵!
他是生过我的气的。
他是建筑业老板,几乎没有机会给我们公司提供服务,他提供的唯一一次服务是维修我们公司和驻地的窗户,活没有多少,要价也不算高。
可是我跟他讲价。
呵呵,讲价是我的习惯嘛,身为财务人员,节俭好像成为一种习惯。
我跟苏丹税务局讲价,跟苏丹工商管理局讲价,跟苏丹污水处理公司讲价,跟苏丹垃圾处理公司讲价,跟所有我要打交道的人讲价。
呵呵,讲价成为一种常态,而且每次都大获全胜。包括跟税务和工商管理部门的讲价,用家乡的土话说,我是蛮能嚼的一个人。仅限于讲价时候啊!特别说明!
而且每次所有被我“侃”价的人都很喜欢我。
可是,我,不应该和苏里门讲价。
我很后悔。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买。
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
“好吧!我不收钱,为你,只是为你!”
他没有着恼的神情,但我感受到了那颗着恼的心。
他坚持再也不肯收钱。
无论我如何的劝说,他不开发票,不收钱。
嗯,几万块不多,但是也不算少。
我无奈的告诉经理,经理说,算了,算了,他不收就算了吧。
我白白地又欠了他这么大一个人情,后悔一辈子。
不过,他还是坚持到我这里“上班”,当我的“编外”。
还是坚持为我跑东跑西,当我的“外联”。
唉,他为我做的事数都数不清阿!
某天,我们聊起了牙齿,我说我的牙齿很好啊,非常洁白健康坚硬结实,用不着去看牙医啊!
他很吃惊,说,“难道你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去看过牙医吗?”
“对啊,我的牙齿很好啊!”
“不,你应该去看牙医。你至少应该检查一下你的牙齿是否真正健康。”
“可是我的牙齿很好啊!”
“这个应该由牙医来说。我会给你预约安排好,带你去看牙的。”他口气坚决,似乎就这么定了。
我一笑了之,并不在意,想着他也不过说说而已。
他却果然约好了下一个周二的晚上,带我去他女友开的牙医诊所看牙。
看牙的结果可想而知,我所谓的健康的牙齿并不健康,有两个已经有轻微的龋齿迹象,难怪有时会隐隐作痛,而且有很深的牙垢,把整个牙龈都包裹住了。
据她女友说,如果我的牙垢不处理,可能几年内这些牙齿都会坏掉。
送我回驻地的路上,他说,“牙齿也是美丽的一部分阿,你这样美丽,一定要重视啊。”
连续一个多月,每周他都亲自陪我去看牙。
在诊室外等候的时候,他总是温柔的看着我,陪我说话聊天,所以等候也不是那么难耐了。
他女友在美国留学了5年,该诊所的设施丝毫不亚于国内的水准。
奇怪的是,看到他对我那么好,他的牙医女友从来没有对我吃过醋,而且也跟他一样对我无比温柔体贴。(这在中国恐怕是不可想象的一种现象。嘻嘻,反正要是我,没准还会吃个小醋的。)
并且所有的诊疗费用是全免的。
我要交钱,他和她都笑着不同意。
我想我或者不该拂他俩的好意。
从此,我半年看一次牙,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
也一天比一天更知道该如何精心对待自己的牙齿,这终身的“伴侣”。
某次,在那个牙医诊所,碰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她在款台付款,有着中国女人特有的婀娜多姿苗条的背影,我正在心里羡慕着,苏里门开腔了。
“这个女人真丑。”
“啊,为什么?”
“你看她的脚踝,多细啊,象骷髅。”
我并不奇怪地笑着,也下意识去看自己的脚,呵呵,我的连着“小象腿”的脚踝是珠圆玉润的吧!
在苏丹,我第一次不觉得自己的胖,因为这里以胖为美。
丰乳肥臀成了美丽的标志,于是白肤的我成了所谓的美人,她们常喊我苏丹第一美女。
我却觉得我买东西时“淘”来的秘书,堪称世界第一美人。她是埃及人,爸爸从前是银行家但是早年去世,家道中落,开一小店为生。
我们的地质员26岁了,从来没有被男人约过一回,因为她太苗条,唉,这要是在中国,她该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阿。
世界就是这样的奇怪。
苏里门的牙医女友不是普通的胖的,我记得来到她的牙医诊所,苏里门指着她女友的臀部让我看,说:“看,多么美!”我哑然失笑。
如果说我的臀部大,那他的牙医女友的臀部比我的大两倍。
我们的另一个地质员常常骄傲的说,我是最美的。我心里不敢苟同,因为当时她带着牙套,也有着巨臀。
她看出我不信任的眼神,强调着,她在苏丹确实是很美的,因为她的臀部。
结婚前,她取了牙套,穿上婚纱,画了妆,我一下子呆住了,惊为天人,白雪公主应也不过如此,我贪婪地看着她,不想丝毫移动自己的眼睛。
呵呵,我可没那倾向阿,只是特别爱美,爱一切美的人和美的事。
有时候特奇怪,看着欧洲的名画中的女人,哪一个不是丰腴圆润白皙无骨的呢,她们那么的美,到了现实中,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人就不是美人了。
呵呵,不过,自从到过苏丹,我知道自己是美的了。
嗯,苏里门,让我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所以理应是我记住一辈子的朋友。
在苏丹,拿驾照是非常难的,据说很多国内专业司机过来也没有过关。
主要因为那个一米宽的90度转弯的必考内容。
经理说,让苏里门给你强化练习一下一米宽90度转弯吧!
于是那段时期的每一个下午的下班时分,苏里门就带着我练习如何在一米宽距内90度转弯。
练习了半个月,苏里门带我去考驾照。
交规是他翻译成英语,我自己填的。
路考特别逗,苏里门开着车子,所有当天要考驾照的学员都在某地集合,突然一声令下,说要今天考驾照的人都赶紧上驾驶位,跟着前面的教练车,于是换了我来开,苏里门坐旁边。呵呵,还没驾照呢,就跟着教练车穿越了整个喀土穆市区,来到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而且所有的车都开得飞快,幸好我曾下苦功练过飞车车技。突然前面的车停了,当天监考的路考官下车说话:“现在开始路考!”我晕。
开了这半天了,说开始路考。
于是一个个排队,路考。
路考开车时间好像还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然后去中心考90度转弯,我看着那么窄小的一米宽的路障,看着绝对90度的弯角,和那辆用来考照的QQ小车,心里开始发怵。
苏里门开始和那边交警模样的人低声交头接耳,然后在场子里这里走过来、那里走过去,和好几个人窃窃私语。
我呆呆地望着别人怎么考,发现很多都没有过关。直接失去信心。
一会儿,苏里门过来了,悄悄说,“不用考了。我们等会儿直接来拿证。”
原来他花了相当于一千五百块人民币,贿赂了考官们。
顺利拿到证之后,苏里门满脸开心的笑容,从车子的那一边把他的车钥匙扔给我,说,“好了,你有照了,你来开!”
呵呵,我又开着车子穿越了大桥,穿越了喀土穆。
在接近驻地的红灯处,嘻嘻,我一下子没有发动着车子,一辆车子飞速超过我们的间隙,司机对着苏里门大吼,苏里门脸红红的。
我问,“怎么啦?”
他朝我做鬼脸,不好意思地说,那是一个将军,他责备苏里门,如果我不会开车,就不应该带我出来,带出来开也不应该在主道上开。
“你怎么知道他是将军啊?”
“他军服上的军衔。”
哈哈,我笑说,将军就了不起啊,真是的!
不过看着苏里门的窘样,我想这个国家的等级制度还是森严的,即使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原来对将军也是尊敬的。
正如我在苏丹呆了两年,总想混进那里的军官俱乐部,却总也混不进去一样。
呵呵,拿了照,我请所有人去酒吧喝酒,当然少不了苏里门,还有各个公司的朋友们,一行二三十人,浩浩荡荡地去了一家很有浪漫情调的高楼顶层酒吧,大家或坐或卧,一醉方休。
我给苏里门讲了爱尔兰咖啡的故事。
他们都笑话我开车象蛇一样歪歪扭扭地爬行。
我不生气。
几周后的一天,苏里门来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昨天开车去银行啦?”
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本来就是好车,再加上美女,谁会不注意呢?
呵呵,在这个封建的国度,我每天穿得跟古装戏里出来的人一样,长袖善舞,长裙飘飘,再加上夸张的带网纱的帽子以抵抗那烈日艳阳,即使不美,或者也是有气质的吧!
常常有人对着我飞吻,惊呼“好莱坞明星来了”。
在苏丹,可能人们最担心的就是疾病了,马来热、埃博拉、黄热、白喉等等时刻威胁着我们,马来热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苏丹人都得过马来热,并且反复感染。
我最怕得马来热。
也有外单位的同行因为得马来热而死去。
可是,在离开苏丹之前两个月,我得了马来热。
那是怎样的一种煎熬,疼痛到骨子里,发烧至头脑不清。
但是心里的折磨更甚。
医院。
验血,检查,发现疟原虫。
我被告知得了马来热。
据说这是能潜伏在人体肝脏二十年的病毒。
医院的大厅开始落泪,我没有哭出声,绝对没有,只是落泪。
瓦里德表情复杂的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
慢慢地我身边聚满了苏丹人,他(她)们问我怎么了,瓦里德说是马来热。
所有人都来安慰我,告诉我,马来热并不可怕,很快就会好,就像感冒一样。
其实我怕的是未来的二十年,也许没准哪天我就又复发了。
七年后的反恐训练,咨询我们请来的曾在热带雨林服役的雇佣军官,他专门讲了关于马来热的一课,他说像我这样算是控制得很好的,七年内没有复发过一次,可能就是完全痊愈了,不会再复发了。
我住院了,来看护我的全是苏丹人,还有另外一家公司的两个中国姐姐。
三天后,我出院了。
回到驻地,大家一起在驻地吃晚饭的时候,同桌的女同事,拿起杀蚊剂,直往餐桌底下喷,这就罢了,我走到哪,她的驱蚊剂就跟着喷到哪。
马来热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母蚊子叮咬传播的,只有有这种母蚊子的地方才能传播马来热,也不是一次蚊虫叮咬就能传染,是无数次被蚊虫叮咬后,疟原虫累积到一定量才会发作。
我和喷我的女同事吵了一会儿就上楼去了。
之后我总是吃了饭就上楼,自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
当然,当时和现在我都能理解,谁也不希望得马来热。
但是说不伤心不失望那是假的,幸好,苏丹人陪我度过了这一难关,帮我度过了这脆弱的心理期。
我收到了来自律师的大捧鲜花,他是被周恩来接见过的原苏丹大法官,我刚去苏丹办理注册新公司事宜时的法定律师,70多岁的健康老人。
我至今记得他赠送的那张卡片上的话,“在我们的村庄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马来热总是感染那些有魅力的女孩。”
其实我们有一年多没联系了,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我得了马来热。
我得到了苏丹女孩们的悉心照料和心理辅导。
苏里门更是每天都来看望我数次,出院后的每天晚上,他都带我出去喝新鲜的果汁,据说新鲜果汁能够帮助马来热患者尽快恢复,并防止复发。
至少是苏里门坚持这么说。
出门走在街上,一路上各种各样的食物,走一路他问一路,想吃这个吗,想吃那个吗,这个很好吃,尝一点吧。
使我想起在武汉读大学时,姐姐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很感动。
渡过那段难捱的日子,苏里门起了重要作用。
想想,苏里门帮我、帮公司做了多少事啊。
电灯坏了,线路烧了,网络不通了,锁坏了,空调不转了,停水了,停电了,所有的琐事,他都积极地联络和安排。
我们一起去过美丽的大坝,一起进过撒哈拉沙漠,一起接待过国内的代表团,他永远是最佳的导游。
记得一次接待代表团,很快和代表团的人成为了朋友。
时间短暂而快乐,代表团回中国了,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
某天,苏里门在我面前拨通了代表团某个朋友的电话,响了三声后,他挂断了。
我问,“为什么挂断?”
他说,“只要知道这个电话接通了就够了,不需要说话。”
是啊,说什么呢?
这或许是一种另类的浪漫。
我始终认为,我和苏里门之间是纯洁的友谊。
苏里门是否对我有那种男人对女人的情感,我是不得而知的。
只记得有一次我说想念尼日利亚的黑人厨师做的比萨饼,他说,我带你去吃喀土穆最好的比萨。
于是晚上,我们出发,他开车。
车子行走在傍晚若隐若现的暮色中,突然他将车停在路边,头伏在方向盘上,声音暗哑的对我说,“我能触碰一下你的头发吗?”
这里他用的是“touch”这个单词,我不知道我这么翻是不是能表达原意。
我说,“不”
他说,“就一下,我轻轻的。”
我说,“不”
“我有老公的。”(当时有老公的,现在没了。)
补充说明。
他说,好吧,发动车子向比萨店飞驰。
我们一起坐下来吃比萨,一切如常。
我和苏里门是连握手都很少的,可能就是初见面的那一次吧。
之后,他还是每天来这里报到,跟从前一样,看不出任何变化。
我的厨房的冰箱里总是被他购买的各种苏丹甜食塞满,但是我吃的很少,因为我觉得太甜了。不过这些零食总是很快被消灭光,因为有一帮饿肚子的下层当地员工呢,他总是会很快续上。
不过他也偷喝我们的酒,苏丹是禁酒的,这些酒都是我们从使馆弄来的。
他只偷喝那些已经开封了的酒。
那年的十一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逃离苏丹。
我被告知三天内结束苏丹的一切事务,立刻奔赴南美。
心中狂喜万分。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另一个男人天罗地网的爱情。
在我心中,他,是恶魔,是种马。
但是离开苏丹,踏上南美的土地之后,我开始怀念恶魔的疯狂追求,这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啊,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三天三夜没合眼,没有以躺倒的姿势呆在任何地方一下下。
夜以继日地归纳文档,做一切收尾工作。
如果有人来看我,我甚至都没时间抬头望他们一眼。
苏里门来了,我匆忙地望向他。
他双眉轻皱,目光忧伤。
突然间,我想起那天的比萨店,他好像也是这样一副神情。
而且发现,这好像是我很常见的一种表情。
他送了我两只象牙镯子。
我还从来没有戴过。
那时候苏丹是不禁象牙制品的。
过去了很多年了。
曾经我给他,苏里门,打过一次电话,那是在厄瓜多尔、基多。
一个普通的清晨。
电话响了三声后我挂断了。
“只要知道电话接通了就够了……”
他的话回响在耳边。
八年前,碰见来自苏丹的原公司的人,问起苏里门。
说是结婚了,找了个富商的女儿。
“是那个苏丹首富的女儿琳达吗?”
“不知道。你走了以后,他再也没来过公司。”
后记:或许写下这个故事在这个浮躁的快餐社会是有点意义的吧,人们的内心深处可能都在呼唤一种长情,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读到。欢迎转发。
封面:尼罗河上大桥
文中配图:1、青白尼罗河交界处
2、某次跟苏里门一起带代表图去大坝拍下的,钻石一样的水面,好像最美的人心。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ibahecar.com/xzqh/80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