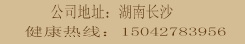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作为东非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作为东非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作为东非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当前位置: 苏丹 > 行政区划 > 作为东非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引言
华斯哥·达·伽马的第四个儿子,名叫克里斯托瓦奥的缪托·根提尔霍门公元年率领了一支远征队来到埃塞俄比亚。他穿着“长统袜和打着绉褶的红缎和金线织就的锦缎外衣,披一件镶金的精致黑色斗篷,头戴一顶别有漂亮徽章的法国便帽”。
他因为这种炎热气候整天吃尽了苦头,他带着大约四百五十名葡萄牙士兵、船长和乡间大佬。他们是应埃塞俄比亚皇帝的邀请而来的,怀着拯救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信仰,帮助把来自索马里兰的穆斯林侵略者驱逐出境的豪迈目的。他们终于获得成功,虽然这种成功得来并不轻易,也不是马上就能收效的,而且是以东·克里斯托瓦奥的生命作为悲惨的代价的。这种成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比穆斯林有更多的火枪,火绳枪在当时是战斗中的一张王牌。这个远征队的一个成员卡斯坦霍萨事后写下了他目睹的情况。
这是一篇很有用的记载。卡斯坦霍萨的记载,虽然并不是有关中世纪后埃塞俄比亚情况的最早最长的描述,但可能是最有趣的一篇。我们通过他的记叙便能抓住埃塞俄比亚历史基本的主题:山地民族在遭到邻国和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顽强的征服之后,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卡斯坦霍萨说出了一个人在看到这个在一千二百年前皈依了基督教的遥远的非洲国家,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仍能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特征之后所感到的惊讶。
这一主题有惊人的持续性。就以涅古斯(皇帝)这个名称而论,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就已出现了。南阿拉伯的一块希姆亚雷特文的碑铭曾提到和哈巴善人国王加达拉特的联盟。这位国王的称号还包括纳加希和“哈巴夏特与阿克苏姆国王”的称号。正是这些哈巴善人,后来在经过沙比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几世纪的渗透和侵略之后,建立了阿克苏姆。他们的称呼也曾经在第十八王朝(公元前年~年)那些叙述与邦特国家进行贸易的碑铭中出现过。
而且,虽然把狮王纠达的兴起追溯到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爱情的传说,显然只是一种虔诚的伪造,但是在它的象征性的本质中,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在那古老的年代里,当推罗的国王希兰的船只上下红海,把俄斐的财富带到以色列去时,埃塞俄比亚的西北部(哈巴夏特的土地)曾经是“邦特和乳香”世界的一部。但这种惊人的持续性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持续性。虽然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它独特的文明,为非洲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这是奇怪的特有的一章。
阿克苏姆,和前次出现过的库施一样,将在一个短期间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但阿克苏姆和被它打败了的库施不一样,对于非洲的其他部分,是无足轻重的。这当然只能是对目前的无知状态作一定保留时才能如此说说。这种保留是相当大的。直到公元前年,波斯人征服南阿拉伯为止,阿克苏姆王国必然曾经对那“远方海岸”上的一些港口,非洲和阿拉伯的海洋贸易的终点站发生过作用。无疑地,还继续在那里起着自己的作用,直到伊斯兰教兴起,封锁了红海海峡,使它只对穆斯林的船只开放时为止。
此后,它就衰落了。从六世纪到十四世纪,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在混战之余从历史的记载中消失了。这些战争包括和北方的穆斯林的战争以及和南方的异教徒的战争。当它在历史上重新出现的时候,仍在进行这样的战争,虽然这时已有停战的希望。但是这时阿克苏姆早已消逝了:占着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山地的阿姆哈里克人和梯格理人,正像今天的情况那样。但如果教条式地把非洲这一地区的历史和其他地区一视同仁将是愚蠢的。
在埃塞俄比亚,刚开始有考古学记载,虽然最近几年,由于目前在位的皇帝的开明态度,已经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尽管迄今为止获得的证据还不够清楚,不够具体,但可以说,许多最初的影响是从这里得到启示的。可能是经过阿克苏姆人和阿姆哈里克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在非洲传播梯田的知识和实践,并把它一直传到了遥远的南方。反映中东非中世纪早期文明的不用灰泥砌合石头的建筑技术,这种建筑在大津巴布韦臻于顶峰,可能是在这里发展起来并传播出去的。
那种建筑椭圆形庙宇或碉堡的方法,是从南阿拉伯,经过阿克苏姆,传到非洲南部的。那种目前仍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被采用的,在男人的墓碑顶上刻一根阴茎作为装饰品,以表示他们的显要身份的习惯,也许可以和西苏丹那种类似的做法追溯到同一个起源。可能西达马(也在埃塞俄比亚的南部)的高大的石阴茎,是和西非的史前巨石,和东非的阴茎形墓碑,和现在罗得西亚的阴茎形小装饰品,都有关系。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都是可能的;其中有一些看来确实可能。但没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在考虑它们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南阿拉伯的闪米特人,在纪元前好几个世纪前就侵入了埃塞俄比亚,并随着时间的消逝,产生了一种埃塞俄比亚文明。这种埃塞俄比亚文明反映了这些闪米特人故乡的文明。现在所知道的闪米特人的最早铭文是在离阿克苏姆不远的叶哈地方发现的。铭文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为异教的女神诺拉和阿希塔尔献祭的祭坛而刻的。这两位正是老所罗门年高昏愦时候,为他的“外邦妃嫔”所诱惑,而错误地崇拜的亚斯他录女神。但是根据更早期的埃及铭文来看,哈巴善人早已就住在这里了。
他们不是闪米特人。这些早期的阿比西尼亚人经过闪米特人的入侵后仍然留存下来。从闪米特人那里学过不少东西,还逐渐地建立了自己的奇怪的、而且带着奇怪的特色的阿克苏姆文明。这是一个遭到侵略的民族,比侵略者存在的时间更长,吸收了侵略者的文化,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另一种文化的又一证明。阿克苏姆依靠红海贸易而繁荣起来。它的港口阿杜里斯在公元七世纪,当一位前来这里访问的希腊人记述关于它的情况时,已经发展得相当大了。而且远在这之前,就和遥远的印度和锡兰发展了商业关系。
商路从阿杜里斯的内地把这种对外贸易继续沿着阿特巴腊河带到尼罗河中游和麦罗埃。并且无疑地,使商业上的尖锐敌对状态挑起库施和阿克苏姆国王之间的争吵。麦罗埃的铭文(至少那些可以看得懂的文句)提到过老早的库施王哈西奥提夫(公元前年到年)和纳斯塔森(公元前年到年)统治的时期,库施就已经进行了反对阿克苏姆的创建者哈巴善人的战争。而结果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阿克苏姆最后占了优势。
大约公元年前后阿克苏姆终于征服了库施。实现了这次征服的阿克苏姆君王艾扎纳斯(或者可能是那个事实上征服者的继承人)对一整队敌人赢得了胜利。他的早期货币是一种用黄金铸造得很精致的硬币,上面有一弯新月和两颗星星,象征他的异教信仰。但是他后期的货币却是一种谨慎的基督徒用的货币,上面刻着十字架。来自罗马帝国东部的拜占庭牧师在这个时候使他改变了信仰。这种改信基督教的行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宗教方面。它有助于使阿克苏姆王国及其阿姆哈里克继承者获得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其他邻人的意识。
这种意识给他们一种巨大的持久力。但这也意味着他们从事的战争是宗教战争。他们加强了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四邻几乎都是穆斯林或异教徒的情况下,陷于孤立。这样,今天那些在埃塞俄比亚占统治地位的阿姆哈里克人的文化和文明,到后来变得和他们国家南方的异教徒文明或者他们北方和东方的穆斯林文明截然不同。这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成为交流思想和技术的障碍。但是埃塞俄比亚的物质生活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说对于发生在南方的或者以后发生的情况可将是重要的,这就是:山坡梯田,在陡峭的山顶建造碉堡或防御工事的习惯和阴茎的象征。
它们一再出现;也可能它们是在距离很远的地方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的表现太有趣了,使人无法加以忽视。在山坡修建梯田和灌溉工程的文化是非洲东部和东南部早期文明一个不可分割的重大方面。这种做法在南阿拉伯很早就已经有了。那里整个雅致结构的光彩,都建在一点点的水能流过很长的距离,以及在陡峭的山坡保持水土的基础之上的。在西边,远至达尔富尔西部地区,现在仍然还能看到这种山坡梯田。这类梯田显然表现了古老历史,只是在很小的规模上还一直继续使用到今天。
年一些调查者发现,从杰贝耳-马腊和杰贝尔-西的下撒哈拉山地直到瓦达依的边界,方圆一万二千哩的地方,都有梯田,只是绝大部分现在已经荒废了。这种梯田被煞费苦心地一直开辟到今天已经没有人居住也无人耕种的杰贝耳-马腊的已经熄灭了的火山的边缘。埃塞俄比亚的山坡梯田是以同样复杂的干劲发展起来的。
年本特在访问梯格理时能对叶哈的景色作这样的描绘:“四野的群山布满了梯田耕地,在希腊或小亚细亚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见过象在这个阿比西尼亚谷地那样规模巨大的山间梯田。过去定有几十万英亩被精耕细作着,几乎一直耕到山顶;而现在,除了一条条整齐的土畦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种梯田耕作法也并不仅限于埃塞俄比亚的北部——沙比、阿克苏姆的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某些修得最成功的梯田,现在发现还在被使用,被修筑,例如信奉异教的康索人就是这样的。康索是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尼格罗人的一支。他们居住的地方,群山也被顺着等高线开成无数曲折的线条。
这种梯田,过去一直以为是非洲北部所特有的,但是后来证明完全不是这样的。现在了解到,向南一直到林波波河,都有一些现已不知去向的人,采用过这种耕作方法。在肯尼亚、坦噶尼喀、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这种方法曾经被广泛地采用过。用石头堆砌建筑物,不用灰泥胶合的艺术是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另一种古老技巧。康索人,正如他们现在还继续修筑山坡梯田那样,目前还在使用这种技巧。东边,越过埃塞俄比亚南部高高的山峰和绿色的山谷,在索马里兰平原上隐藏着许多用石头和砖修建的中世纪城市的废墟。关于这些城市的确切归属、起源和历史,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
年寇莱对非洲文化交织之谜作了又一次贡献。他在倒塌了的长满荆棘的砖头建筑物中发现了一些三角形的壁龛,直到今天还可以在达尔富尔以及西至库姆比-沙勒(很可能是古代加纳首都一的遗址)的一些年代较久的建筑物中看到这种建筑形式。我们又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实:目前看来在完全互相隔绝,似乎从未有过共同历史的国家之间,却有过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目前的表现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也再一次无法说明这种影响传播的方向、时间和方式。
古代埃塞俄比亚许多以阴茎为象征的纪念碑又是一种明显的特征。从亚的斯亚贝巴向南,在那慢慢向北肯尼亚令人窒息的平原倾斜的西达马和博腊马陡峭的山谷中,人们可以遇到许多刻作阴茎状的独石碑。这些石头,有十至十二呎高,有时候上面刻着一些线条和一些无法解释的符号。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什么也没有。看来它们不像墓碑。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现在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这些石头的情况。在这些高高的花岗岩独石碑的附近,和其他的一些遗址中,还有一些耸立的石块。
这些石块有的经过雕刻,有的没有,可能都是和那些独石碑是同时代的,也可能是更早的时代的产物。它们经常刻成宝剑或匕首的形状。但匕首状的看来似乎是属于较晚的年代的,而且并不能就此认为这种独石刻成的匕首,同青铜器时代欧洲的斯通亨季或卡那克地方的年代肯定更要久远的雕刻成的匕首会有什么紧密的渊源关系;虽然奇怪地,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容易引起联想的特点。年,埃塞俄比亚的亨丁福特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石头的年代。但是,也许它们并不属于同一时代。
有一些,像阿克苏姆的刻花古石,可能还有一些剑状的石头,能够追溯到阿克苏姆时代,而另外一些,包括那些阴茎形的石头,可能是属于较近的年代的。”但是它们的影响,或者类似影响的东西,似乎一再出现着。在南罗得西亚和安哥拉,甚至远至南非洲的巴苏陀兰都可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仅仅是由于这是一个富于平坦的山顶和陡峭的山坡的国家显而易见的最好的防御方法吧。也许它们还意味着是一条“文化漂流”的路线,因而也是迁移的路线。只要考虑一下两个惊人地相仿的描述: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另一个来自两千多里(可能还要更多一些)的德兰士瓦的北部。
公元年克里斯托瓦奥·达·伽马前来拯救埃塞俄比亚王室时,发现太后住在德勃腊达马险峻的高山的平顶上(事实上,这种位于安全地方的建筑物在古代埃塞俄比亚是常见的;有时,还被用来当作把潜在的王位的竞争者撵到乡下去的方便的所在-这实际上无异于监狱)。当时在场的卡斯坦霍萨说,通向德勃腊达马山顶去的坡道,是一条起自山麓的曲折的小道。但是,就从相当于“八十”高的三分之二,或五百呎的地方-岩石突了出来,瞰临山麓上方,他们只能坐进一只从岩石中凿通的窟窿中吊下来的篮子里,才能上达山顶。
年年底,在非洲的另一端,德兰士瓦北部的荒野里,一个名叫范格兰的农夫兼采矿人偶然发现了一处值得研究的所在。据说,从林波波河南岸高低不平的地带升起的一座平顶山上可能发现宝藏。范格兰和他的儿子有很长一段时期找不到能够向导他们爬上这座奇怪的山岭的人。因为这座山似乎是不可攀登的。后来,他们终于设法诱导一个当地人指引了一条显然是秘密的、通向山顶的路。在年这还是一条完全为树木掩盖的、狭窄的山石裂缝,或者可以说是烟囱。当他们开出了一条道路走到裂缝下时,惊异地发现,过去使用它的人曾在裂缝两边凿了一些小洞。一根根的梯木就可以插在这些小洞上。范格兰设法从这个烟囱中爬上山顶。
马庞古布韦的宝藏,就终于通过这个途径公诸于世了。现在还不能说在德勃腊-达马同马庞古布韦之间曾经有过任何思想联系,或者说它们之间需要有这样的联系。我们只能说,如果山顶碉堡和住宅,是在不同地点和时间完全独立地进行建筑的话,在这里再一次产生非常相象的结果。但把这些结果和不用灰泥砌合石头的高超的建筑技巧,梯田耕作以及间或显著地使用的阴茎象征等加在一起,的确可使人毫无疑问地认为:长时期内,曾经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有过思想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对于古代非洲南北移徙大势的这一背景,尽管人们小心谨慎,这一带有极其清晰明显结论的证据,总要使人对之产生巨大的惶惑不安。面对一种无法解释的思想的共同性,面对一些民族和文化,它们移动的路线和相互了解的限度看来比文物发现所能允许的程度更为宽广、更为直接,人们似乎觉得奇怪。
当人们从埃塞俄比亚向南推移,遇见肯尼亚、坦噶尼喀和罗得西亚的梯田的遗迹、津巴布韦的围墙和塔、涅克克和英扬加的住宅和马庞古布韦金制殉葬品时,这种惶惑不安的程度就更为增加了。但是,对于这种由于清晰明显的结论而产生的惶惑不安,正如在较早的时期要欧洲人相信非洲人绝不可能修建这样的围墙、塔和梯田时所产生的类似的惶惑不安,用不着感到失望或沮丧。
结语
借用卡通·汤普森一句发人深思的名言。这只能使人增加对于这些遗址和遗物,以及它们作为了解非洲过去的残缺不全的阶梯的作用所发生的兴趣:“它丰富了,而不是削弱了我们对它们出色成就所感到的惊讶。(而且)它不能贬低他们固有的威严。”因为它的神秘“是一种埋藏在非洲当地地跳动着的心灵深处的神秘”。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ibahecar.com/xzqh/124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