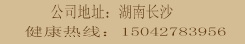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苏丹 > 当地气候 > 佩里middot安德森雷蒙德mi
当前位置: 苏丹 > 当地气候 > 佩里middot安德森雷蒙德mi

![]() 当前位置: 苏丹 > 当地气候 > 佩里middot安德森雷蒙德mi
当前位置: 苏丹 > 当地气候 > 佩里middot安德森雷蒙德mi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摄于年。
本文首发于《新左评论II》第一百十四期,年11/12月刊。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逝世三十周年,威廉斯主编的《五一宣言》出版五十周年。
佩里·安德森,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至年、至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荣休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近著有《原霸:霸权的演变》。
《上海书评》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此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左翼在英国崭露头角,其中公认最有影响的两位智识分子是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一位是文化理论家,一位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作为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他们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学生时代加入了共产党,二战期间,二人皆服役于坦克团,战争结束后从剑桥毕业。年,汤普森第一次加入英国共产党,直到年因匈牙利事件才与其分道扬镳;威廉斯复员后没有重新入党,组织上不再隶属于后者。冷战期间,汤普森在北部工业区,威廉斯在南部海岸区,各自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威廉斯出了一本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研究(),汤普森出了一部威廉·莫里斯的传记()。年夏天,在退出英共之后,汤普森和他的历史学家同事约翰·萨维尔(JohnSaville)创办了《新理性者》(TheNewReasoner,它的副题是“一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季刊”),吸纳了其他的——现在是前——共产党智识分子,以及像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这样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威廉斯
二战时的汤普森
年秋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ety),立刻声名大噪。在一片好评声中,最严肃的交锋来自维克多·基尔南(VictorKiernan)——另一位前共产党历史学家——发表在《新理性者》的文章。其时,威廉斯已经开始为《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andLeftReview)供稿,后者是一群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更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刊物,该创刊集体的形成可上溯至五十年代——而非三十年代。年,两份刊物合二而一,变成了《新左评论》(NewLeftReview),由斯图亚特·霍尔任主编,并伴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合作办刊:汤普森是编委会主席,威廉斯是编委会成员。
《新理性者》(创刊号)和《大学与左翼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新左评论》第一期和第二期
一
次年春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的续作《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其中部分内容,早在前作本身问世之前,就在《大学与左翼评论》上刊登过了。这本书涉猎范围更有抱负,形态构造更加理论,结论方面更具政治性,无疑需要《新左评论》予以重视,于是,霍尔邀请了汤普森撰写书评。汤普森有些勉为其难,他担心一旦表达了自己同威廉斯的分歧,便有可能让新左阵营陷入分裂,而这是他意欲避免的。霍尔回复道,与汤普森所虑正相反,左翼需要公开的辩论——霍尔的好意占了上风。在接下来的两期《新左评论》,年的5/6月刊和7/8月刊,汤普森在这份刊物第一阶段(firstincarnation)最具有思想分量的稿件里,回应了《漫长的革命》,这是一篇足以与他四年后对其第二阶段的著名批判——《英国人的独特性》(ThePeculiaritiesoftheEnglish)比肩的论说文。汤普森写道,对于新左翼,威廉斯是“我们最出色的一员”,在冷战最恶劣的那些年,共产主义文化受到日丹诺夫主义荼毒,马克思主义僵化为官方教条,建制思想纷纷采取一种洋洋得意或秋后算账式的保守主义反应,虎狼环伺中,威廉斯是他这一代里唯一留在社会主义思考领域里的人——“我简直无法形容这么做需要何等锲而不舍的智识耐力”。“[威廉斯]身后是一个妥协的传统,手里是一堆破碎的词汇,于是,他做了剩下唯一能做的事:接管对手的词汇,尾随他们进入其论述核心,以彼之术语还之彼身,打得他们举步维艰。他为年轻人开出了生路,现在,他们又一次沿着这些道路前行。年,当他看到一些社会主义同辈人回到他这一边,他的笑容里一定带有一丝讽意。”(《论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新左评论I》,第九期,年5/6月,24、27页)
《文化与社会》的年代版本
这一成就,汤普森继续道,并非全无代价。威廉斯在这十年里没有默默无闻。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调性(tone)问题。因为持续与艾略特,以及其他同时期的一众声音唱和,他在重建《文化与社会》考察的那个思想传统时,呈现出某种“去教堂礼拜似的庄重”,脱弃(disembody)了书中诸位彼此远非和睦相容的政治或个人激情。但这同时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威廉斯多少接受了对手们看待他们关切的问题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对于社会主义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把文化定义为“整体性的生活方式”(wholewayoflife),这在太大程度上受惠于艾略特,即便他对其做了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改造,也依然如此。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那些永远分隔生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冲突和阶级斗争。威廉斯选择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演示《漫长的革命》的步骤,但他在再现这个时代的时候,没有提彼得卢屠杀以及之后的驱逐,没有提爱尔兰大饥荒,没有提宪章运动在政治上的惨败。取代这些痛苦的历史倾轧的,是一系列出现得过于频繁的抽象概念。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成长”(growth)——《漫长的革命》的通关密语:该词旨在追踪一场仍在进行的、未完成的全面社会转型中,大众读写能力、文化、民主组织的累积性拓展,涵盖这一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结构,或者用威廉斯的术语,它的“维持系统、决策系统、学习与传播系统、生育与养育系统”。
《漫长的革命》初版本
成长,在威廉斯慷慨地赋予该词的意义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样的十年——也不光是这十年——这个术语会令人误入歧途。“苦难不仅仅是成长边缘的耗损,对于受苦者,它是绝对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9页)同样,将一个社会的诸系统分成四份,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去想一想马克思是如何构想这些关系的,这样的四分便不会有生产性。《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间接讨论(obliquerunningargument)”。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马克思从未被正视过”,尤其在如是异常奇怪的旁白中:威廉斯声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文化或家庭从来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样的错误颇能说明问题,于是,悖论便是,威廉斯“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力,一直与他自身与社会主义智识传统的部分脱离相伴随,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后者的结果”(《新左评论I》,第九期,30、24页)。威廉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投入是毋庸置疑的,《漫长的革命》的结论对此有极好的表达。但是,他的这些抽象概念(它们所隶属的词汇,部分源自那些反对任何这样社会的人),却有碍于理解如何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什么可能挡住了通往那里的路。
《漫长的革命》,[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月出版,页52.00元
因为——“如果现在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那可以假定,这场革命既有反对的东西(阶级、制度、人、观念),又有支持的东西”。在威廉斯的表述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无外乎一组模糊的委婉之词:“常见的旧社会形式的惰性”“非民主的决策模式”“支配性的方式”,凡此种种。而被这些说法压抑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伴随着“一路以来对冲突和损失的充分体察”而从未丢掉的,便是“漫长的(或是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的危险”。在威廉斯笔下,这从未被表达过:“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要用一页纸来掩盖到年的日子,那么关于德国制度的成长和壮大,差不多也能讲出一个同样的故事。甚至在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就像《文化与社会》里没有外国人,《漫长的革命》里也没有外国:维柯和韦伯在前者缺席,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后者缺席。一场革命可以持续多久,汤普森问道,“既不在反革命面前屈服,又不会走到社会主义的人的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之间爆发危机的那个节点”?——在这个危机点,“‘革命’与‘成长’这两个术语便无法兼容”(《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第十期,年7/8月,39页;第十一期,年9/10月,未编页码)。确实,汤普森自己[关于革命]的概念常常被认为是太过末日启示(apocalyptic)了。但威廉斯的,则或许过于寡淡乏味了。
刊有汤普森《漫长的革命》书评的两期《新左评论》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威廉斯的原创性需要在传统之外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尤其如今,这个传统内部杂乱无章”。自年以来,在各种波动变化的左翼观念中,“有两个一贯的主题:雷蒙德·威廉斯(包括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的写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价值重估”(《新左评论I》,第十期,34、37页)。如果想让它们走到一起,使新左翼获得智识上的聚合,二者之间必须有一场关于权力、传播、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是汤普森致力于开启的。威廉斯是一个如此有力量、有原则的思想家,同他进行批评的交锋是无法回避或推延的。但愿——虽然并非必然——双方关于革命概念的分歧会在辩论中变小,新左翼的两股潮流能够汇聚在一起。
汤普森《漫长的革命》书评
阐述生动,论证清晰,汤普森此文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漫长的革命》具有罕见深度的批评性回应。就其严肃性,其对于展开对话的提议而论,它欢迎威廉斯的回复。但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可以肯定,霍尔作为杂志的主编,会敦促威廉斯写一篇答辩,而他拒绝了。当在大约二十年后被问及原因时,他表示,汤普森说了“一些必要且正确的东西”。把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把冲突排除在外,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少左翼书写中,存在着某种误导性的对于“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混淆。前者是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利益矛盾,后者是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观意愿,是当“结构性冲突变成自觉的、相互的争夺,变成公然的力量交锋”的时刻。前者是永久的,后者是偶发的。“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进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就不得不避开或省略所有冲突以其他形式调停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冲突被临时地解决或暂时地搁置。”五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很卑微的时期”。汤普森并没有充分看到这个差异:“我在爱德华的写作里感觉到了一种对于历史上英雄的斗争时期的强烈情感,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情感一经表达,却特别不适合处理那个我们刚刚度过的非英雄的十年。”(《政治与文学》[PoliticsandLetters],伦敦和纽约:Verso出版社,年,页)
《新左评论》对威廉斯的访谈录——《政治与文学》(年初版,年再版)
那为什么威廉斯没有在与汤普森的对话中发展出这一至关重要的论题呢?倘若存在这么一场对话,新左翼明显可能会受益良多。他说了两个理由。在右边,《漫长的革命》遭到了猛烈攻击,让人不禁回想起到年间的气氛。在左边,汤普森文章里的“一些题外话和口气(tones)”,反映出其基本无力做到“既保持理论分歧,又呈示共处同一阵线”,从而使一些本来站得住脚的论点,沦为不那么有力,实质上有论辩意味的(polemical)见解。身陷两边的交叉火力,“实在不知道要面向哪边”(《政治与文学》,页)。所以他决定保持沉默。
威廉斯的沉默是因为汤普森的评论吗?很明显,它伤了威廉斯的心。但无疑,这里推波助澜的还有两人之间的误会,他们都误读了对方的口气。从一开始,汤普森就解释了他将本着何种态度来写作:他批评了威廉斯呈现《文化与社会》主人公的方式——就好像威廉斯要形构一个如此得体的大写的传统,在它面前,“任何一丁点儿的笑闹声或论辩声”都不合适。他引用了威廉斯的格言,当“你能听到停顿和努力:即一个人诚心诚意(ingoodfaith)聆听别人并作出回应时所必需的坦率和诚实(honesty)”,你就在“真诚交流”(genuine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ibahecar.com/ddqh/6719.html